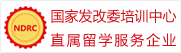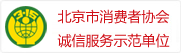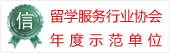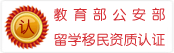在纽约,田朴珺尝试过普通留学[生的生活,住租来的房子,一个多月花四百美元,吃路边摊。 受访者供图
在纽约,田朴珺尝试过普通留学[生的生活,住租来的房子,一个多月花四百美元,吃路边摊。 受访者供图
去美国读书 闲下来是浪费生命 新京报:你在已经生意小有成就的时候,去上长江商学院[,又去美国读书,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精力和时间来学习? 田朴珺:可能跟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因为我小时候家教非常严,从礼拜一到礼拜五,除了上学之外,我的课余时间全都在补课,周末我也要上各种辅导课。我已经习惯于我的生活被填得满满。有一段时间我回上海家里没什么事干,看到旁边有一个魔术班,我还跟人家学了三天魔术。就是觉得闲下来应该学点什么,不应该长时间的空在那儿,我觉得是一种对生命的浪费。 新京报:有的人留学是为了去镀金,有的人是想改变目前的生活状态。这些在你看来都不太成立? 田朴珺:可能对我来说最大的放松就是每天收拾屋子的时候。我解决烦心事的方式,就是拿抹布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拿纸巾把家里的踢脚线擦得干干净净,好像把污浊的垃圾扔掉。所以我享受把每天排得满满的,让我没有时间去考虑我有什么不满足的。 新京报:学英语挺难的,做投资也需要接触数学方面的知识。你在学习过程中,怎么克服学这么专业的知识? 田朴珺:我是很感性的一个人,逻辑性很差。对我来说可能演戏更像我自己,因为它是感性地挥发你对角色的理解,你只要顺其自然去演。但是做生意是另外一套逻辑思维,对我来讲真的挺难的。一开始我做的时候,我曾经去给一个投资公司打工,朝九晚五的白领生活。可能我有一点点同龄人没有享受过的过程,就是我十八九岁以后不曾去过迪斯科,没有去过夜店。我觉得自己天生过着50多岁人的生活状态,一直在比较平和的状态里。 新京报:不管是做演员,还是做生意,大家想象中都是接触夜生活,你完全没有? 田朴珺:完全没有。我真的没有喝过一口酒,甚至啤酒。我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前世可能是喝了很多酒,歌舞升平死的,所以这辈子对这事天生不感兴趣。我记得18岁生日,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问可不可以去次迪斯科。然后在上海就跟几个朋友去迪斯科过生日,大概半个钟头,就出来了。我跟我妈说震得我心脏难受,不太喜欢。我更喜欢的方式就是三五个好朋友,大家坐在一起聊天,那个是我特别喜欢跟人交谈的状态。可能因为我心脏不是特别好,我受不了那种特别吵的环境。 留学生活 租十几平米房子当普通学生 新京报:去美国学习的时候,遇到实际的困难了吗? 田朴珺:我就是过一个简单的留学生的生活,每天坐地铁,走路。在北京你有车有房子,当时在纽约也没住的地方,到处去找房子,租房子。我记得当时租的房子没有空调,没有窗帘,我都快疯了。但是因为我临时去租房,只能找到这种条件的房子,马上要搬进去,不然就得睡马路了,所以坚持忍着自己戴一个眼罩。当时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哪有卖窗帘的。然后没有空调,特别热。因为我那个房子很小很小,大概十几平米。有一个小的厨房,但是没有抽油烟机,因为老外做饭很少有油烟,所以我也不敢在那儿做饭。 后来热得实在受不了,只能打电话给房东,我说你能不能给我装一个空调。房东说行,第二天人就来了。我看那空调大概十几年没用过。他说你热的时候就开这个,不热的时候就关一下,交一百块钱就行了。结果晚上打开的时候,震得根本无法睡觉。我只能把门关上,开着它,尽量保存冷气,等我睡觉的时候把它关上,平时能不开空调就不开。
新京报:以你的经济情况完全有条件可以住更好的房子,你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过穷留学生的生活?
田朴珺:对,有那么一点点自虐式的状态。家教给我的感觉是,最牛的人是要跳得了龙门,也要钻得了狗洞的。所以我觉得那样的状态对我来说没什么大不了。那时我身上没带什么美元,我跟我一个姐姐打电话,告诉她我银行卡只剩四百美元。当时他们听完第一反应是用不用我给你汇点钱。我说不要,这四百美元挺好的。后来就这样花了一个多月。
我跟朋友说我在美国的生活状态,他们都不相信。但我觉得很好,尤其我在纽约有一个半月没有坐过汽车,只是靠走路和坐地铁。记得有一次看到有车开过去,突然有种原来有车是很奢侈的事的感觉。同学之间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没有人知道你到底在一个什么经济状态下,我不想有什么特殊化,所以我觉得过这种普通留学生的生活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