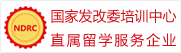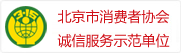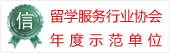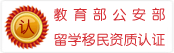小时候的朱迅能言善辩,有着主持天分。1987年,14岁的朱迅第一次“触电”,担任中央电视台《我们这一代》的小主持人和校服模特。第二年,她又阴错阳差地出演了电影《摇滚青年》里的小小。接着,这部电影红了,小朱迅也红了,片约接踵而至,电影学院甚至抛来了诱人的橄榄枝。就在众人认为朱迅正走上“星光大道”的时候,这个17岁的孩子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放弃一切,去日本留学。当时《摇滚青年》在全国放得正火,朱迅留学之事引来了电影学院老师们的一片惋惜声。可是年轻气盛的她,自认为出身于书香门第,满腹清高,一定要向自己的大姐、二姐一样,出国镀镀金,所以她毅然地推掉了5部电视剧的片约,决心东渡日本。在日本,这个自从上了高中以后就没再向父母要过钱的挣钱“老手”,也体验了一把挣钱的艰辛。
1990年十七岁的朱迅告别了祖国到日本留学,因为不是公派留学生,她的留学生涯是半工半读性质的。在日本,朱迅的房东是一个凶巴巴的女主人,养着一条残了左眼的老狗,虽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但朱迅几乎不敢和她家来往。后来,房东告知她房子要翻修,希望她尽快搬出去。可是,朱迅白天要上学,晚上打工,没有多余的时间和钱再找房子搬家。再加上,租金高得实在无法承受。好不容易找到一处便宜的屋,人家一听是中国留学生,笑成一条缝的眼睛圆了,“我们不租给外国人。”门重重地关上,心被夹得生疼。那时候,在异国他乡,朱迅体会到钱是维护自由和尊严的一道最有力的屏障,“除了学习外,我要挣钱!挣很多的钱。一连几个晚上,我闭着眼睛在床上算计。”
日语学校里除了韩国、马来西亚的那几个富家子弟外,几个日语稍有底子的同学都先后找到了小时工,中午买饭时,能毫不犹豫地要上一份500日元的鳗鱼饭。朱迅一边吃着250日元的青咖喱,一边托付几个要好的同学,“如果打工的地方有空缺,别忘了给小妹推荐推荐。”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几天,那位天天吃鳗鱼饭的同学就告诉朱迅,他打工的地方正招人。朱迅换上自我感觉最好的那件蓝印花连衣裤,兴高采烈地跟着他去面试。在电车上晃晃悠悠了近一个小时,又用课堂上刚学的半生不熟的日语跟领导套瓷,领导终于答应先让朱迅不带工资试用一天。
当朱迅拿起抹布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一份清扫厕所的工作,和一位四十来岁的日本女人一起,打扫从1楼到18楼的所有厕所。朱迅在《说出来就过时》里,这样写到当时的心情。“听说是扫厕所,我脑子有点懵,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干过。但想想自己交了语言学校的学费,钱包已经瘪瘪的,而自己还要为上大学积攒120万日元……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拽着拖把跟在后面。”
9月的日本,闷热潮湿,厕所中没有空调。女厕比男厕要脏多了。下班后,留在这里的是刺鼻的臊臭,几乎要让朱迅把一个星期前在北京吃的饭都吐出来。用手把纸篓中的脏东西一个个掏掉,再用抹布把便池旁溅出的屎尿擦净。这一刻她鼻子一酸,泪水夹着汗水一滴滴地掉进了便池里。从1楼到10楼的清扫,已经让朱迅累得直不起腰了。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最不能忍受的是日本妇女对她的怜悯,对她来说,这是一个伤害。
一次在朱迅打扫厕所的时候,一位40岁左右、身着和服、打扮得很体面的太太走了进来,她没看见地上的水,脚下一滑,一个踉跄向前倒去。为了让日本妇人不至于摔倒,朱迅一把抱住了那妇人的双腿,日本妇人摇摆了几下总算站定。但是雪白的日式足套已被溅湿。朱迅的一双脏兮兮的手印已经完完整整的留在了上面。和朱迅一起工作的妇女怕极了,连忙的鞠躬道歉。道歉是可以的,但她却忍受不了日本妇人的轻蔑态度。阔太太招呼朱迅出去,从包里拿出两个精致的饭团,施舍般的递给朱迅,小声的说:“可怜的。”这短短的三个字,深深刺痛了朱迅,对于一向高傲的她来说,这是振聋发聩的伤害。
朱迅当时就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着那妇人优雅地走开。可是,还没到大门口,只见妇人的女儿拿出一张湿纸巾给妇人擦手,好像在埋怨她怎么去碰一个扫厕所的外国人。那妇人擦完手,顺手把它丢进了垃圾桶,还回头看了朱迅一眼。一股不可阻挡的寒意涌上心头,走回厕所,朱迅看着手里的两个饭团,泪水奔流而下。“天哪!这就是我要接受的现实吗?”朱迅狠狠地把饭团扔进便池,不停地按着冲水钮,水声轰隆,奔流而下,掩盖了呜咽声,冲走了骄傲,也惊醒了樱花梦……
像所有出国留学的学生一样,明星们在国外的生活也少不了打工这一项。像所有的打工生活一样,明星的打工生活也少不了眼泪和委屈。但经过这样历练后,才能发出更加耀眼的光彩。但是,此时的朱迅,生活中已经没有了掌声,没有了喝彩,面前只有看不完的脸色,背不完的日语单词。随着日语水平的增高,她不停地更换工作,生活总是上学,打工,回姐姐家,三点一线。由于过度的劳累临考大学前朱迅病倒了,手里攥着医院的诊断书,是血管瘤,医生说得很肯定,这个病不能等,最好马上做手术,朱迅吓得满头是汗。
为什么会得血管瘤?朱迅自己也不知道,可能是太累了,也可能是长期心情压抑,憋的。马上回国吗?不行,半途而废,如何见江东父老。于是,朱迅决定还是留下。为了省钱,朱迅躺到了一家私人小医院的手术台上。贪便宜的结果是手术失败,坏东西没全拿干净。不幸中的万幸,切片的结果是良性,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但是为了筹集高额的学费,刚刚出院刀口还没有完全长好的她又开始了新的打工生涯。
终于,咬牙苦拼让朱迅赢得了回报。在1991年10月通过了日本文部省日语验定的最高级“一级”,有资格考大学了。上大学不久,NHK(日本广播协会)中国语讲座在招收新人,朱迅当时根本没有打算进入日本的艺能圈,只是想在电视台打工,每小时的收入可能会高一点儿。可是当她第一次走进NHK的演播厅,试着站在主持台前时,心中那把熄灭了三年的火又燃烧了起来,她喜欢这个职业!
NHK如同中央电视台一样,节目的知识性强,台风较为严谨。与中国的文艺界相比,日本艺能圈更讲究长幼尊卑,等级分明。每个“大腕”在节目中都有非常强的表现欲,很讲排场。在这个礼数要求极严的圈子里,朱迅又一次以“外国人”这一独特的身份胡打莽撞地闯了过来。日本电视台的《亚洲观》 ,富士电视台的《Hey!Hey!Hey!》,东京电视台的《音乐大拍卖》等等,朱迅主持过各色各样的节目,也见了五湖四海的人。人们开始庆贺朱迅是在多家日本电视台有固定节目的唯一的中国籍主持人。
拿到硕士学位的那一年,朱迅的生活又起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母亲病重住院”的电话让远在海外的三姐妹心急如焚,分别从加拿大和日本同时赶回了北京。回到北京,看到病榻上的母亲,不禁泪水涟涟。妈妈真的老了,厚厚的纱布缠着她的双眼,医生说有失明的危险。而且由于过度劳累,妈妈的脖子里长了两个大血瘤。半年之内,妈妈三次开刀。在这三进三出之中,那么坚强的妈妈,她的身体被彻底地击垮了。为了照顾病重的母亲,白发苍苍的老爸也日渐不支。两个姐姐已经远嫁海外,有了自己的孩子和家庭。只有朱迅是个自由人。不久,专攻市场学的电视人朱迅做了一个让自己都很吃惊的回国决定。
当朱迅向经纪人提出要回北京的时候,她不住地对朱迅说:“你冷静点儿,你冷静点儿!”从此朱迅开始筹备回国的事,国内的最大的电视媒体首屈一指当然是中央电视台。在国外有人说“出国容易,回国难!”习惯了在国外的生活,想在国内谋得一个满意的工作的确不易。正巧《正大综艺》节目招聘主持人,很幸运,在严格的考试中,朱迅获得了优秀成绩,正式成为中央电视台国际部的节目主持人。
回头看看走过的路,从17岁到27岁,这段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朱迅把它留在了日本,10年岁月曾经苦过也曾经乐过。但最重要的是使她学会了怎样去拼搏,懂得了什么是责任。不论在哪里,人生本来就是不断劳苦的过程。因为只有通过劳苦来开拓快乐。“劳苦”和“快乐”的总和就是这10年的青春岁月。
本以为所有的事情都顺风顺水,朱迅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舞台上,谁知走进中央电视台才发现这里的一切和日本完全不同。“在日本所有的画面都是固定的,每一个镜头,甚至会有分镜头剧本;而在中国,一切都是灵活机动的。最关键的就是在日本做主持人,稿子都是有提示牌的,但是在中央台却要主持人脱稿,这也是衡量主持人业务水平的标准,所以自己必须从头学起。”
“其实刚回来的时候,觉得很可怕,这些主持人的记忆力太惊人了!五点钟拿到稿子,7点上节目居然牢记于心,我却连记个开头都很困难!”当时她刚从日本电视台辞职归国,多年的留洋经历让她的中文表达能力退化了不少,站在台上词不达意的压力让她经常回到家中嚎啕大哭。当语文老师的妈妈给她出招:重读中学语文课本。从《岳阳楼记》到前后《出师表》。
于是,朱迅就利用休息的时间背古文,在节目间隙背,睡觉的时候也背,看别人的节目,也在自己的节目中找问题。在这样的努力下,朱迅一步步走了过来,成为《正大综艺》、《周末喜相逢》、《神州大舞台》等热播节目和大型晚会的主持人,并且在2009年、2011年连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她还获得了中国播音主持界最高荣誉“金话筒奖”。如今,家中上万册藏书是朱迅的骄傲,而莎士比亚作品是她的最爱,刘震云、莫言的书她也百看不厌。